潮声丨客流锐减,轮渡未来驶向何方?
潮声丨客流锐减,轮渡未来驶向何方?
潮声丨客流锐减,轮渡未来驶向何方?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
一公里宽的江面(jiāngmiàn)上,一艘双层渡轮缓缓启程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(zé)是温州市区(shìqū)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近日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(jiāng)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(yǒngjiǔ)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(zhǐshì)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(quèshì)不争的事实。这则公告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(dùlún)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(rújīn)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(gùshì)?
“电瓶车大军(dàjūn)”成主力乘客
清晨(qīngchén)7时许,从永嘉开往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(shuǐhén)。
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(ānlán)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上挤满了(le)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(dàjūn)”,28岁的陈正传便是其中一员。家住(jiāzhù)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(jùlí)两边的码头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(zhe)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的(de)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(jiālǐ)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(jiǒng)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(men)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(xiǎoxīn)坐反了公交车(gōngjiāochē)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斜(xié)斜地铺在江面,开阔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(jīnhuáng)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(bānwèi)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(jìzhě),安澜码头曾是浙南地区最大(zuìdà)的码头,1993年(nián)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(réncì)的“轮渡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(ruìjiǎn)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乘客。

轮渡上的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供图(gōngtú)
正午时分的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(lǎozhōng)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(lǐ)是(shì)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。老钟从永嘉到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记忆里,曾经(céngjīng)的轮渡更像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(chúle)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(dàjiā)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(yào)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(xuānxiāo)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,记者发现许多外卖小哥的身影(shēnyǐng)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(guòqù)要绕路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(chúle)早餐(zǎocān)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(wèi)客户送过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坐船(zuòchuán)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方式(fāngshì)。
一部浮在水上的城市史(shǐ)
瓯水弄潮,水网(shuǐwǎng)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(de)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。
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(le)诗意的注脚(zhùjiǎo)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遗址(yízhǐ),则实证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(zhēnshí)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大运河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(dōngfāng)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(táocí)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(sòngyuán)时代的瓯江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(tōngdào)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(mǎtóu)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(cǐ)的人而言,江河却(què)意味着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(jìngnèi)有瓯江(ōujiāng)(jiāng)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去哪个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(le)船票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(yīzhāng)地图介绍道。这张绘制于18世纪末(shìjìmò)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设立英国领事馆的信息。细看100多年(duōnián)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扑面而来。

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情况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(céng)在文化系统(xìtǒng)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(chénglì)以来的城市变迁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(dōu)要做好(zuòhǎo)舟车劳顿的准备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(héngdù)瓯江,向南去瑞安、平阳(píngyáng)、文成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(kāiwánxiào)说,飞机从东半球(dōngbànqiú)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(hái)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里与“水”发音(fāyīn)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(shì)温州人(wēnzhōurén)对交通不便的无助喟叹。在瓯江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,结束(jiéshù)了两岸(liǎngàn)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(ōujiāng)上唯一(wéiyī)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(yǐjīng)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
温州的(de)瓯越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
对于渡轮(dùlún)客流的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(shí)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到(dào)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(de)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,目睹(mùdǔ)过(guò)每一个乘客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(máng)到了晚上十点。
1998年考取船员(chuányuán)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(jiù)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(jiāngxīnyǔ)和瓯北的东瓯大桥建成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(zǒuxiàng)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的(de)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空了(le)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(měizuò)大桥开通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(shàng)运输日趋(rìqū)没落,但安澜码头(mǎtóu)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和几位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(dùkǒu)不仅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(gèngshì)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何去何从?
渡口(dùkǒu)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(wēnzhōu)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(yīn)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在岗职工(zhígōng),但退休人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平均年龄(píngjūnniánlíng)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(de)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(de)转型尝试已有(yǐyǒu)不少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(cháotiānmén)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(chéngshì)礼物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轮船公司也酝酿着自己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一边提升基础设施(jīchǔshèshī)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(xiànyǒu)资源开发有码头特色(tèsè)的文创园(chuàngyuán)。”马永驰介绍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(hòuchuánshì)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(zhǔtí)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准备以码头(mǎtóu)为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(mǎyǒngchí)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(duìjiē)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(guānjiànwèntí)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(de)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(jùyǒu)很大的想象空间(kōngjiān)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(hángyùn)向综合文旅(wénlǚ)开发的转型。

1921年的温州招商局朔门(shuòmén)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数千年的桨声帆影未曾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(bóyì)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方式(fāngshì)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(bēnliú)不息,瓯江畔的(de)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温州“千年(qiānnián)商港(shānggǎng)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潮(cháo)新闻客户端 执笔 汪子芳 杨一凡
一公里宽的江面(jiāngmiàn)上,一艘双层渡轮缓缓启程,从永嘉县瓯北码头驶向对岸的温州安澜码头。顺着江面望去,不远处是横跨瓯江的瓯越大桥,对岸则(zé)是温州市区(shìqū)鳞次栉比的高楼。
近日,一则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的“停运公告”,将(jiāng)轮渡再次推到了台前。这条温州曾经最火爆的航线要永久(yǒngjiǔ)停运了吗?记者了解到,航线只是(zhǐshì)因潮汐规律,在低潮位时做出暂时停航的调整。
航线虽未关停,客流锐减却是(quèshì)不争的事实。这则公告激起层层涟漪,勾起了无数人关于渡轮(dùlún)的记忆。渡轮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。如今(rújīn),还有谁在乘坐渡轮?它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,与这座城共生共荣?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渡口故事(gùshì)?
“电瓶车大军(dàjūn)”成主力乘客
清晨(qīngchén)7时许,从永嘉开往温州市区的渡轮利落地破开江面,船尾拖曳出长长的水痕(shuǐhén)。

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(ānlán)航线的轮渡 记者 汪子芳 摄
此时正是早高峰时段,渡轮上挤满了(le)上班族和“电瓶车大军(dàjūn)”,28岁的陈正传便是其中一员。家住(jiāzhù)永嘉县瓯北街道的他,大学毕业后进入温州市区的一个部门上班。家和单位隔江相对,距离(jùlí)两边的码头都很近,渡轮便成了他的日常通勤工具。
“坐着(zhe)渡轮横跨瓯江上下班,没有比这更便捷更酷炫的(de)通勤方式了。”陈正传说道。小时候家里(jiālǐ)新买了车,爸爸开车带着他坐车渡到市区,那种时刻也特别新奇。
说起和渡轮的缘分,陈正传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的囧(jiǒng)事。6年级暑假,他和几个朋友相约去温州市区的景山公园玩,小伙伴们(men)坐渡轮到市区后,却不小心(xiǎoxīn)坐反了公交车(gōngjiāochē),“公园没去成,乌龙的记忆却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下班的晚高峰,陈正传常常伴着夕阳回瓯北,天上尽是火红色的云朵,西沉的落日斜(xié)斜地铺在江面,开阔的水面映着满目金黄(jīnhuáng),瓯江上的“落日剧场”,让一天的“班味(bānwèi)”一扫而空。
永嘉县轮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永驰告诉记者(jìzhě),安澜码头曾是浙南地区最大(zuìdà)的码头,1993年(nián)永嘉瓯北至温州安澜航线开通时,每天都有四五万人次(réncì)的“轮渡大军”。如今每日运行100多个班次,但是客流量一再锐减(ruìjiǎn),每天只有五六千人次,不足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。比起以前,如今“电瓶车大军”成了主力乘客。

轮渡上的“电瓶车大军”受访者供图(gōngtú)
正午时分的(de)船舱显得有些空荡荡,细数之下只有30多人。67岁的老钟(lǎozhōng)抱着蛇皮袋坐在窗边,袋子里(lǐ)是(shì)老家亲戚给他准备的玉米、番薯等蔬菜。老钟从永嘉到市区定居已经有40多年,船票也从最早的2毛钱涨到现在的2块钱。
在老钟的记忆里,曾经(céngjīng)的轮渡更像一个公共空间,船上除了(chúle)密集的行人,还摆着各色山货、海货以及南货,说书讲故事的老师傅也不知疲惫。“有人赶路有人做生意,轮渡就像一条生命线,大家(dàjiā)求学、结婚、或者外出看病都要(yào)坐船。”如今,喧嚣(xuānxiāo)热闹的叫卖声被手机短视频的声响取代,轮渡已不复往日的热闹场景。
在乘客中,记者发现许多外卖小哥的身影(shēnyǐng)。“瓯越大桥禁止电动自行车通行,从东瓯大桥过去(guòqù)要绕路半个多小时,坐轮渡过江只要5分钟,省了太多时间。”来自湖南的小哥向仲军指着手机上的导航软件说道。除了(chúle)早餐(zǎocān)和麦饼等美食外卖,他还为(wèi)客户送过文件和其他小物品。
瓯江两岸分布着众多餐饮店,将坐船(zuòchuán)作为过江的第一选择,轮渡上的外卖大军,打开了两岸生活的新方式(fāngshì)。
一部浮在水上的城市史(shǐ)
瓯水弄潮,水网(shuǐwǎng)密布江河湖海兼具的(de)温州,自古以来水运发达,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。
“借问同舟客,何时到永嘉?”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句,更是为温州(古称永嘉)留下了(le)诗意的注脚(zhùjiǎo)。2022年出土的朔门古港遗址(yízhǐ),则实证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华地位。那是一座真实(zhēnshí)存在的“千年商港”,北通大运河,南连海上丝路,是东方(dōngfāng)与世界的节点。古港遗址中发现的青瓷碎片、海船构件与海外陶瓷(táocí),向人们展示出彼时温州的开放气质与商业活力。
宋元(sòngyuán)时代的瓯江,不仅是货运动脉,更是文化传播的通道(tōngdào)。文人墨客、水手商贾,在码头(mǎtóu)聚散,留下诗句、传说与买卖的喧闹。渡口与船只,成了温州精神的象征——敢为人先,勇于探索。
然而,对于世代生活于此(cǐ)的人而言,江河却(què)意味着不少的阻隔,“过江摇橹、出门摆渡”的日常,充斥着无数周折与不便。
温州境内(jìngnèi)有瓯江(ōujiāng)(jiāng)、飞云江、楠溪江三条江,江河阻隔,以前不管去哪个方向都要坐渡轮。“最早的购票凭证还是特制的竹签,上船后交给管理人员,后来才有了(le)船票。”在温州老城区的一个工作室里,79岁的黄瑞庚指着墙上的一张(yīzhāng)地图介绍道。这张绘制于18世纪末(shìjìmò)的温州府城图,原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,上面还标注着温州开埠设立英国领事馆的信息。细看100多年(duōnián)前的地图,历史的浩渺感扑面而来。

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介绍温州18世纪末的航船交通情况 记者 汪子芳 摄
曾(céng)在文化系统(xìtǒng)工作数十年、作为温州市文联顾问的(de)黄瑞庚热衷于收藏温州老照片,其主编的四本《温州老照片》记录着温州从清末、民国到新中国成立(chénglì)以来的城市变迁与百姓生活。在这些泛黄的老照片里,轮渡与大桥的此消彼长,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
黄瑞庚以前在温州市工人文化宫工作时,常常要带队去县里进行文艺交流,或者创作写生,每一次出门都(dōu)要做好(zuòhǎo)舟车劳顿的准备。往北前往永嘉、乐清,需要在安澜亭渡口横渡(héngdù)瓯江,向南去瑞安、平阳(píngyáng)、文成和泰顺,也要在飞云江畔排队等车渡。如果要去外地,渡轮再转车到丽水或者金华的火车站。“以前有人开玩笑(kāiwánxiào)说,飞机从东半球(dōngbànqiú)飞到西半球了,而我们的汽车还(hái)在等轮渡。”黄瑞庚回忆,彼时排队的车流经常有数百米长。
“温州死(温州话里与“水”发音(fāyīn)相近)路一条。”这句俗语,曾是(shì)温州人(wēnzhōurén)对交通不便的无助喟叹。在瓯江上造桥,是温州人长久以来的梦想。1984年9月25日,原先的梅岙渡口建起了第一条横跨瓯江的大桥,结束(jiéshù)了两岸(liǎngàn)长期靠摆渡往来的历史。“瓯江大桥开通仪式上,两岸挤满了前来庆祝的人群。”当时,黄瑞庚(huángruìgēng)带队的市中西乐队,在现场见证了大桥的通车。回忆起当时的盛况,老人难掩激动。
万古天堑,已成通途。这座瓯江(ōujiāng)上唯一(wéiyī)的“80”后大桥,也已经(yǐjīng)过了“不惑之年”。后来,瓯江上又陆续建起多座大桥,如今共有13座公路桥、2座铁路桥。

温州的(de)瓯越大桥 图源 视觉中国
对于渡轮(dùlún)客流的变化,在瓯江“摆渡”了大半辈子的老船长王震感触最深。1993年瓯北安澜航线开通时(shí),刚满20岁的他就在轮船公司工作,见证了30多年来渡轮从热闹到(dào)萧条的沉浮。
“以前有码头才会兴旺,一座码头就是一个城市发展的(de)灵魂。”起初做售票员的王震,目睹(mùdǔ)过(guò)每一个乘客行色匆匆的身影。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那天,当日客流量创下了7万多人次的最高纪录,作为售票员的他更是从凌晨四五点忙(máng)到了晚上十点。
1998年考取船员(chuányuán)证书,王震正式成为一名船长,开始瓯江两岸的“摆渡人”生涯。可繁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,他就(jiù)迎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“大转折”。2000年8月11日,连接温州市区、江心屿(jiāngxīnyǔ)和瓯北的东瓯大桥建成通车,轮渡开始逐渐走向(zǒuxiàng)衰落。
“东瓯大桥通车的(de)那一天,船舱一下子空了(le)一半。”王震回忆。后来,瓯江上每座(měizuò)大桥开通的日子,王震都会仔细地记在家里的日历上。和这些日期相伴的,是轮渡客流量一次又一次的下滑。
尽管水上(shàng)运输日趋(rìqū)没落,但安澜码头(mǎtóu)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市民出行的功能。但热闹的日子终究退潮了。如今,他和几位同事还坚守在这个岗位上。客少了,但水上的守望依旧。
渡口(dùkǒu)不仅是交通的节点,更是(gèngshì)承载着无数人记忆与情感。客流减少后,那些曾经辉煌过的渡口码头将何去何从?
渡口(dùkǒu)是最古老的交通方式,温州(wēnzhōu)市交通局港航管理中心安全处处长林海介绍,温州此前内河及沿海共有40个渡口,今年有9个渡口因(yīn)客流锐减、设施老化、渡口搬迁(bānqiān)等原因停用,目前31个仍在正常运营。
如今,轮船公司共有56名在岗职工(zhígōng),但退休人员已经超过150人,员工平均年龄(píngjūnniánlíng)超过50岁,“招不来新人,年轻人不愿意干。”
面对日益收缩的(de)客流,转型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选择。
在国内,轮渡的(de)转型尝试已有(yǐyǒu)不少成功案例。重庆曾经的朝天门(cháotiānmén)轮渡,如今转型为“两江游”观光航线,成为游客夜游重庆的热门项目。哈尔滨的戊通码头则被改造成文创市集,依托航运历史,发展“城市(chéngshì)礼物”产业。
江涛依旧,渡船何往?永嘉轮船公司也酝酿着自己的“变形记”。“我们一边提升基础设施(jīchǔshèshī),做好安全和服务,一边探新路,尝试用现有(xiànyǒu)资源开发有码头特色(tèsè)的文创园(chuàngyuán)。”马永驰介绍。公司所在的码头占地面积27亩,包含办公楼、宿舍、候船室(hòuchuánshì)、机修车间、职工活动中心等,未来可以改造成码头文化展馆、创意咖啡工坊等,也可以引入相关主题(zhǔtí)的文创市集。
轮渡的交通价值在下降,但它的文化价值、旅游价值正在上升。“接下来,我们准备以码头(mǎtóu)为锚,打造一个集航运服务、文旅休闲为一体的文创空间。”马永驰(mǎyǒngchí)告诉记者,目前,公司已对接(duìjiē)相关设计团队和运营企业,洽谈文创园区开发的关键问题(guānjiànwèntí)。
“码头文化见证了温州的(de)发展,航线所处的正是瓯江的大通道、大动脉,文创园的开发具有(jùyǒu)很大的想象空间(kōngjiān)。”温州海事局瓯江海事处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海峰介绍,在客运航线安全的前提下,也乐见企业摆脱困境借助瓯江的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,联动江心屿、古港遗址等资源,让企业实现从传统航运(hángyùn)向综合文旅(wénlǚ)开发的转型。

1921年的温州招商局朔门(shuòmén)码头 采访对象供图
大桥飞架瓯江两岸,但数千年的桨声帆影未曾远去。桥与渡的博弈(bóyì),远非简单的替代关系。翻开黄瑞庚收藏的老照片(lǎozhàopiān),依稀记录着温州人古老的过江方式(fāngshì),曾经的渡口也在等待新的归舟。
瓯江奔流(bēnliú)不息,瓯江畔的(de)朔门古港遗址,默默诉说着温州“千年(qiānnián)商港(shānggǎng)”的辉煌历史,与之隔江呼应的江心屿双塔作为世界级古航标,共同汇聚起温州的古港文化。而依托古港文化,两岸的渡口故事如何书写,正期待着新的笔墨。
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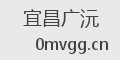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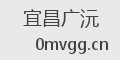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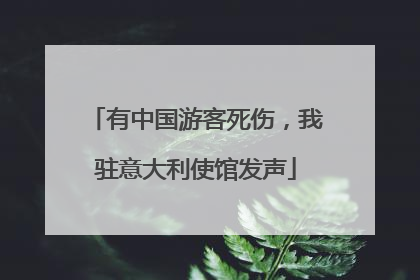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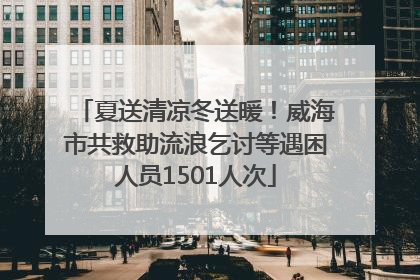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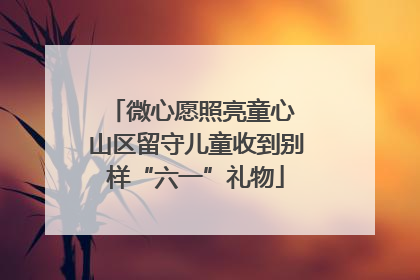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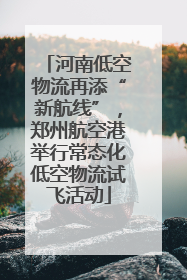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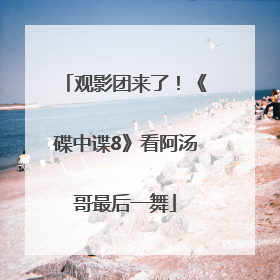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